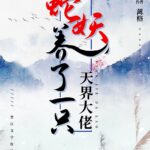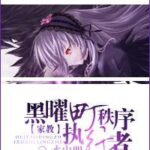第54章栖雲(中)
元化十年,十七歲的蘇松雨遇見二十歲的諸青,在一個無聊透頂的宴會。
他飲了很多酒,又在高臺上吹了太久的風,頭昏腦漲,莽撞地将諸青誤認為樂伶。他貿然闖入,又毫不吝啬地奉上自己的錢袋,颠三倒四得說着贖身之類的話,像栖雲樓中最常見的醉鬼,喝了幾兩上頭,就想上演些救風塵的庸俗戲碼。
但這個醉鬼竟然還記着禮節,他說這些話的時候,一直盯着地面,連頭都未曾擡起過。
這讓諸青覺得好笑,她已經很久沒碰見能讓她發笑的事了。
然後,少年茫然擡起了頭,在她戲谑的問候中,搖搖晃晃,一頭栽倒在地上。
再然後,蘇松雨在自家卧榻上醒來,聽到老仆念叨着,公子去赴宴還是莫要貪杯,昨日竟醉酒迷路,闖到伶人的居室中去了,伶人受驚事小,公子要是有了輕浮浪蕩名聲事大……
他頭痛欲裂,并不是因為老仆的喋喋不休,而是因為他已經全然記不清昨天的事,他出了花廳,登上臨風臺,聽到有人彈琵琶——似乎是邊城月,然後呢?他冒失地去尋樂音來處,彈琴的是誰?
蘇松雨想不起來了,他腦海中只有一個淡淡的輪廓,以及他倒在地上時,瞥見的雲青色的袍角。
其他的細節,他遍尋記憶也拼湊不出來,到最後,他甚至懷疑那首冷清孤寂的《邊城月》,是他酒意上頭的極端時刻産生的幻覺。
直到兩個月後,他去了西市一家書肆。
這家書肆藏書并不算多,但勝在範圍廣泛,許多冷僻的孤本都能在此尋到,是以這家規模雖不大,但在京中文人圈子內有一定名氣。
書肆設在西市最熱鬧繁華的街,終日人來人往,嘈雜不堪,租金亦不菲。蘇松雨第一次站在書肆挂了粗布簾子的門口,仰頭看着牌匾上随意的“滌塵齋”三個字,覺得此處的确有幾分特別。
他掀開簾子,舉步跨了進去,向夥計道清了來意。
“《霧堂筆記》?公子來對了,整個長安也就我們這兒有,請随我來。”
他跟着夥計進了一個裏屋,又進了一個裏屋,屋內四角皆是書架,上面整整齊齊排滿了書冊,蘇松雨不禁咋舌,滌塵齋從外面看,店面并不算寬敞,未曾想裏面竟別有洞天。
夥計在一排排書架上尋了片刻,面露窘色:“真奇怪,我明明記得這本書一直未售出,怎會尋不到?”
蘇松雨見狀,安撫說他今日無事,不趕時間,可以幫忙一起尋找。
于是七拐八拐,他們來到一處偏僻的小室外,夥計剛要進去,卻聽得前堂又有新的客人至,蘇松雨揮揮手示意他去忙,而後自己推開了門。
陳舊木門發出“吱呀——”一聲響,他大步走了進去,一擡眼,發現屋內已經有了一個人。
那個人靠着窗斜斜坐着,在看一卷書,她穿着素綠色的衣裙,與身後花窗中的綠意朦胧成一片。她聽到聲響,也擡起頭看了過來,蘇松雨愣愣地看着她,他認出了這雙淡漠的眼睛。
眼睛的主人一眨不眨地看着他,他當下便手足無措起來,看到這雙眼,兩個月前的回憶瞬間就回到了他腦中,他猛然記起了自己當時有多莽撞。按理說,既然有緣相逢,他該賠禮道歉才是,但是萬一人家早就忘了這茬——
“是你。”窗邊的女子淡淡開口。
“是,是我,”蘇松雨結結巴巴地說,“兩個月前,某喝醉了,唐突了姑娘,實在是某的不是,在此向您賠罪——”
那女子又笑了,她一笑起來,整個人就沒那麽冷清,像月亮邊上朦胧微黃的光暈。
她說:“無礙,你無須放在心上。”說着,她垂下頭,繼續專注于手中的書本,不再說話。
蘇松雨卻因為那個笑容而愣神。
此處的書冊散亂地堆積在櫃上架上,看上去比別處陳舊得多,陳墨的香氣夾雜着灰塵的味道。夥計遲遲不來,他在這種令人舒心的的味道中翻找了許久,一無所獲,直到窗邊的女子突然問他:“你在找什麽書?”
這便是他們交游的開始,那本書原來一直在她手中拿着。
多奇妙的際遇,他們在這間飄着細細灰塵的小室中呆了一個下午,他們聊《霧堂筆記》,聊筆記作者的英年早逝與默默無聞,聊當朝還有多少文人願意嘗試這種詭谲險峭的文風。
他們交換了名字,這才發覺原來彼此早已對對方有了欣賞。清竹居士之名他一直有聞,她的許多詩文是他曾經細細品味賞析過的。只是她并不是好交際之人,所以來長安一年,他并沒有機會遇見。
而諸青說,她也讀過蘇松雨的文章,那是他初來長安時所作的兩篇賦——《清平賦》、《歸鳥賦》。這兩篇是他在同一日寫的,其中《清平賦》讓他打響了自己在長安士子圈中的名聲,衆人皆贊他這篇文氣極高,辭藻華美。
諸青卻直言不諱,她說《清平賦》雕琢痕跡過甚,這兩篇中,她更喜歡《歸鳥賦》一些。說着,她随口誦了其中兩段,并贊它們淡而有味,情真意切。
蘇松雨來長安,已經聽過許多形形色色的誇獎,但沒有任何一次讓他像現在這麽滿足與自傲,事實上,他也更喜歡《歸鳥賦》,他甚至想不明白為什麽世人獨愛另一篇,那篇他根本沒有用心。
他們又談了許久,從詩文到吃食,到天南海北的見聞,諸青去過許多地方,尤其是西北的荒漠高山,在她描述之中有着亘古的遼闊與荒涼,令他神往。而他是姑蘇人士,小橋流水、曲院風荷的景致亦令她贊嘆。
他們當然也聊琵琶,聊那首凄清哀涼的《邊城月》,這竟是他們共同最愛的曲子。他說起琵琶大家顧樸之,這位傳奇藝人在天狩年間的動亂後,隐居在江南,而他是蘇松雨的老師。諸青卻說,顧樸之還有一個師姐,二人技藝不相上下,諸青的琵琶是她一手所授。
如此說來,竟算同門。蘇松雨忍不住微笑,他們有諸多不同,卻又如此相同。
期間夥計進來詢問過,滌塵齋的主人也來打趣了幾句——那竟然也是位女子,諸青似乎同她十分熟絡,二人語氣親密而自然。
直到日薄西山,燦燦的紅霞綴在窗邊,照得室內一片暖意,他們才收了談興,向對方道別,并且沒有約定下次見面,對于這樣如故友般投契的相逢,人們總是有自信,日後還會再遇。
滌塵齋有許多他感興趣的孤本,若有需要,他一定會來,如若沒有,他也會來。諸青是這裏的常客,他們時常碰見,然後一聊一整天,那件僻靜的書室成了他們秘密的聚會地點。
她真的是個很特別的人,蘇松雨不止一次在心裏面想,要尋得一個如此的知己,是多麽的難,而他又是多麽幸運。
來長安這幾年,他已經徹底膩煩了這裏,可是因為她,他開始覺得一切還有期待,他無比希望這份情誼能夠長久下去。
他為此有些忐忑,那天,他試探地問她:“不知清竹成家後,我們是否還能如今天一般談天說地……”
諸青當時在飲茶,聞言,只輕輕吹了口茶湯上的浮沫。
“如若不出意外,我此生都不會成家。”
蘇松雨因為這句話有一瞬間的愣忡,心裏是喜悅還是不安,他無從分辨,只笑着說:“那如何才算是意外?”
諸青便也笑道:“倘若聖人一席話下來,要将我指婚給某人,便是天大的意外了。”
二人便一齊笑了起來,為這無傷大雅的輕松玩笑,但蘇松雨卻知道,他的心沉重了數刻。
她不願成家,除非聖人閑極無聊要關注一個小小民女的婚事,除非太陽打西邊出來。
至于為什麽不願,他不會問,這是屬于友人的距離,他一向把持得不錯,正如他們從天談到地,有些話題卻從不提及。
她是那樣好,那樣特別,他絕不會再唐突她。
而正是因為她那樣好,他們又那樣投契,所以他悄悄愛上了她,這一定不是一件很令人費解的事吧。
元化十四年,蘇松雨會試高中,同年,他在殿試中奪得進士及第,是那一屆的探花。
年輕的探花有着玉人之姿,他打馬從朱雀大街一路到杏園,所經之處皆是驚豔喟嘆,聽不完的贊美之聲,數不盡的錦繡前程,這理應是他一生中最風光的時刻罷?
但只有他自己知道,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,鋪天蓋地的熱鬧裏,他在馬背上,想尋見的只有一個淡青色的身影。
他最後都沒有尋到,所以他成了這份熱鬧中唯一的傷心人。
後來,蘇松雨才知道,那天她突發急症,昏迷不醒,根本無力出門。他一直知道她身體有不适,他怎麽可能沒注意到她蒼白的面容與嘴唇,以及身體不正常的消瘦,可是他問她,她只說無礙。
甚至當他站在了她的病榻前,她也只笑着說無礙。
這也許會是她不願成家的原因,他心裏隐隐有了猜測。
若真是因為疾病,那這病該有多麽可怖,他寧願是其他的任何一個原因,他為這個猜測而心碎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