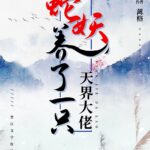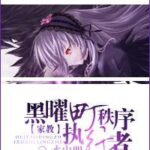第55章栖雲(下)
諸青第一次遇見蘇松雨,卻是在元化十年的春天。
那是三月的某一天,惠風習習,日頭正暖,柳絮漫天地飛。她在滌塵齋二樓靠窗的桌上飲茶,對面是多年摯友,也是滌塵齋的主人。
她們在聊這個月即将印刷的詩集,書齋主人正苦惱于書頁紙張的選用。
諸青捏着茶杯,慢悠悠道:“若黃荊紙造價太昂貴,雨棠何不考慮松皮紙?二者紋路相似,顏色相近,完全可作為替代。”
名喚雨棠的書齋主人卻嘆道:“我如何沒想到這一層?只是去年凍災,各地松皮産量銳減,現下松皮紙的成本并不低,只能……”
她話還未說完,樓下陡然傳來一陣喧嘩,将未盡之言打斷。
二人便望窗外看去,只見晴朗朗天色下,一群年輕人正從對面的酒肆出來,各個錦衣玉帶,神采飛揚,彼此笑鬧着,似乎相約着要去郊外騎馬。
諸青淡淡看了一眼,便回轉了頭,雨棠卻仍看着那群人,她忽得笑道:“我記得,那篇《歸鳥賦》很受你的喜愛——”
她沖着樓下努努下巴:“那作者便在此其中,清竹猜猜看,是哪一位?”
諸青就又擡眼去看,她的目光在那群鮮衣怒馬少年郎中逡巡半晌,停留在其中一個人身上。
那個少年無疑是其中最為出衆的,姿容清俊,如芝蘭玉樹般挺拔。他不聲不響,和一群同樣年少的人站在一處,硬生生把他們襯出了聒噪。
于是諸青隔空點了點那個少年,雨棠順着她手指的方向看去,撫掌笑道:“清竹真是厲害!竟一下就能認出來。”
諸青微微一笑,心道果然。
“真是奇了,你是如何看出來的?你們之前沒見過面罷?難道是僅瞧他長得俊?原來清竹也是這般膚淺之人……”
對面的友人仍喋喋不休,諸青懶得理會,她端起茶盞,輕輕抿了一口。
長得俊?的确是很俊的,但這只是其次。
她回想起剛剛那一幕,周圍的少年興高采烈,熱火朝天,他站在人群中,明明也是清朗卓絕的樣子,但是——
在這輕松愉快的時刻,他的眼神裏只有一片漠然,顯得如此格格不入,而她捕捉到了這個瞬間。
一個少年,在衆好友的簇擁之中,在三月的輕暖春風裏,為什麽會有這樣的眼神?莫名其妙地,她覺得那片質樸簡單、而又有淡淡寂寥的《歸鳥賦》,合該出自于這個人之手。
竟然真被猜中了,諸青飲盡杯中清苦的茶水,她想起這個少年的名字,蘇松雨,字靜篤。
致虛極,守靜篤。萬物并作,吾以觀其複。她自然知道《道德經》中這句話,真是人如其名。街對面的少年們相攜着遠去了,她輕輕一笑,便不再去想這件事。
這是她第一次遇見蘇松雨,蘇松雨并沒有看到她。
同年秋的某天,諸青在栖雲樓。
栖雲樓有她年少時的閨中好友,她們相識時,都還是天真爛漫的小女孩。她們一同繡花習字,偶爾會偷看一些話本,最大的煩惱是将來嫁個什麽樣的郎君,那時寵愛着她們的父母尚且在世,世界對于她們來說像個柔軟安逸的花園。
後來,柔軟不複存在,花園被焚毀,在殷紅的血色與刀鋒的冷色中,她們被迫成長,走上了截然不同的道路。
整整四年,諸青剃發茹素,刺血抄經,奔波在為父親平反的道路上,她為此作了上百篇詩文,或情詞懇切,或字字泣血,它們在士林中廣為流傳。就是那個時候,她漸漸傳出了才女、孝女的名聲,也是那個時候,她在辛勞頓苦中染上了肺疾,并且難以治愈。
而她的閨中密友,芙瑤,與她有着同樣的遭遇,甚至更為惡劣。在父母兄長赴死,族中無人敢救濟之後,芙瑤被充入教坊司,最終留在了栖雲樓。她名字被登記在冊,要重獲自由,難如登天。
那天,諸青去樓裏尋她,二人發生了不算愉快的對話,芙瑤負氣離去,諸青留在芙瑤的房中,在等待她的間隙,彈了一首《邊城月》。
在心煩意燥的時候,她喜歡彈琵琶,這樣能讓心重歸安定。輕緩冷寂的琴音中,她的确慢慢安定了下來,也引來了一個不速之客。
生得好看的确是很占便宜,即使在對方酩酊大醉,眼神虛浮的境地裏,她仍舊一眼便認出了他。
直到二人成為了朋友,在滌塵齋聊了不知多少的天,有一件關于那天的事,她始終沒有告訴他。
她其實,很為那天心動。
她看他搖搖晃晃地走來,雙手奉上的錢袋展示足了誠意,他在醉意中仍維持着禮節,她知道能寫出《歸鳥賦》的人定不是什麽輕浮浪蕩子。所以她任憑自己為少年那份莽撞又克制的矛盾心動,為那一腔不管不顧的孤勇心動,她再沒有這樣的孤勇,所以她很應該為此心動。
但也僅此而已了,她有許多秘密不會同他說,而這是其中最大的一個。
那年,蘇松雨當了探花使,他打馬經過瓊林宴時,她不在人群之中。
因為病症突如其來的加重,她在借住的舅父家中昏迷不醒,無法參與他人生之中的榮光時刻,她為此感到遺憾,但她毫無辦法。
所以當蘇松雨站在她榻前,詢問她的病症的時候,諸青只是笑着搖了搖頭,說她無礙。
她一直知道自己活不長的,在為父母奔波的那幾年,病痛已經深入了她的身體,名醫早早斷言她活不過二十歲。而她如今二十三,已經是很賺,她的人生已有很多遺憾,實在沒有必要再給別人帶來遺憾。
更何況,那是她十分喜愛的人。
那場疾病耽誤了她兩三個月,那段時間裏,她基本都在病榻上度過。蘇松雨順利入了光祿寺,事務繁忙,他仍偶爾來看她。
碰上她清醒的時刻,他們就像以往一樣談天,說風物,說人情。她精力不濟,沒有力氣說話,他就彈琵琶給她聽。如果她在沉睡,他便在房中默默呆一會兒再離開。
他的琵琶彈得不錯,彈起來的樣子也好看,那段時間她并不算太過難熬。
難熬的是他離開長安那三年,蘇州知州蘇長耀突發急症故去,蘇松雨作為他唯一的孩子,必須回蘇州丁憂三年。
那三年,他們沒有見面。
他不能離開蘇州,她因為疾病也不能遠行,但他們時常有書信往來,在信中對彼此問候關懷。
在夏天,他寄來太湖中生長的荷花花瓣,将其風幹後在上面題了一首詩。秋天,他收集西山銀杏金黃色的葉片,她拆開信件,灑落一地的便是姑蘇的秋意了。
她為這些不動聲色的溫柔而失神,如果說她不能感受到其中的愛意,那一定是說謊。
但那又怎麽樣?她的确熬過了這一個寒冬,但下一個、再下一個呢。她已經接收到了自己身體發出的訊號,那并不是什麽吉兆。
于是她始終緘默,直到元化十六年,蘇松雨又來了長安,重新入了光祿寺,他先前的職位竟一直未被替補。
真是意外,他不止一次對她說過不喜歡長安,她也以為他去了蘇州就不會再回來,但他還是回來了,她想她知道原因,那并不難猜到。
元化十六年,蘇松雨二十三,諸青二十六,他們依然是朋友,偶爾見面,偶爾說話。
那一年,諸青的病情有所好轉,她的身體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輕盈有力,也不再會動不動咳嗽,就在一切似乎都要好起來的時候,她遇見了一個道人。
那是一個年輕的女道,修長高挑,廣袖寬袍,頭發潦草地紮着,眼神裏總是似笑非笑。她在滌塵齋之中見到了這個女道,雨棠說她們兩個是故交。
然後——女道為她算了一卦,算成之後,卻眼神躲閃,顧左右而言他。
在再三追問下,她才透露——諸青已經時日無多了。
諸青并沒有多少意外,也不怎麽傷心,她早早地就在等待這一天,只是如今,她有些擔心那個青年。
如女道所說,一個月後,諸青開始急速衰弱下去,她差點就死在了那個冬天。
但她終究沒有,她活過了春分,又活過了谷雨,在三月的某一天,她覺得身體又開始變得輕盈,她知道是時候了。
那天,她和蘇松雨見了一面,他們在小院子中說了半個時辰的話,如從前的任何一次一樣,不過這次,她将跟随自己多年的琵琶贈與了他。
她說是因為最近彈不出好曲子,不算多高明的借口,但他似乎相信了。
他們最後一次見面,是在四月初的簪花宴上。那是他們第一次,也是唯一一次在大庭廣衆下處在同一場合。
簪花宴在春天舉辦,以賦詩為主題,風雅又有趣味。場地之中會準備大量時令鮮花,衆人輪流賦詩,若接得好,便能獲得一支花簪在頭上,結束時。誰頭上花最多,便是這一次的花君。
這次簪花宴是京中一名頗有名望的老儒舉辦,邀請了大半個文人圈,蘇松雨與諸青亦在此列。贈琵琶的那天,諸青說她不會來,所以當蘇松雨在臨風臺上看見她的時候,很是意外。
他到的時候,已經有些晚了,臺上四周挂了輕薄紗簾,在四月和風中漫飛。蘇松雨慢慢拾級而上,然後在紗簾翻開的一角之中,瞥見了女子月青色的衣袂。
片刻的驚訝後,他很快就想通了關竅,主辦人在她為父親平反的過程中幫了不少忙,于情于理,她還是來了。
同旁人寒暄兩句後,蘇松雨慢慢喝着案上的酒,隔着人群,他遠遠地看她,她也對着他微笑,笑容中有些狡黠,她似乎比以前還要瘦了,坐在飄飛的紗幔前面,像是随時會乘風飛去一般。
有伶人在廳堂的屏風後彈琵琶,這種正經詩會上,是不會有那等聲色環節的,彈琵琶便只是彈琵琶,蘇松雨抿了一口酒,他聽出來,此時彈的是《關雎》。
關關雎鸠,在河之洲,窈窕淑女,君子好逑。
求之不得,寤寐思服,悠哉悠哉,輾轉反側……
一首古老的曲調,唱着求不得的遺憾,這份遺憾在世上并不算稀奇,在千年後仍能叫人感同身受,他蘇松雨,不過是千萬落寞人中的一個罷了。
酒香清冽,四周的來賓已開始作詩吟誦,他飲了一杯又一杯,他默默地想着,自己其實不配有多傷心,因為他甚至沒有去“求”,所以理所應當“不得”。
他們相識七年,彼此之間只有克制,那些溫柔或是熾熱的話,他說給月亮聽,說給三月的春風聽,唯獨不會說與她聽。
他們都是聰明人,有些話即使僅放在心裏,彼此都會懂得。就如此刻,詩宴正酣,推杯換盞,滿座的高談闊論間,《關雎》凄婉的樂聲裏,他們隔着熱鬧遙遙相望,都讀懂了彼此眼中的孤寂。
輪到他作詩了,蘇松雨起身,朝着諸青的方向舉起了酒杯,她的身邊坐了不少女官,沒人知道他這杯酒只是在敬她。
“惆悵東欄一株雪,人生看得幾清明。”
“愛惜芳心莫輕吐,且教桃李鬧春風。”
“桃花流水窅然去,別有天地非人間。”
每吟出一句,便滿堂喝彩,在衆人的贊聲中,他桌子上的花枝堆積得越來越多,已經是當之無愧的魁首。
賓主皆歡的盡興時刻,他用衣擺兜着那滿桌的花,慢慢踱到了高臺邊,不顧周圍驚訝的目光,他将滿懷的花枝盡數從欄邊灑落,投入江上輕暖的春風裏。
人們都看他,他卻指着江邊那一叢叢茂盛的竹林,它們翠色的枝條上此時挂滿了剛剛落下去的花,芍藥、迎春、海棠,在風中沙沙作響。
清俊的青年顯然是有了醉意,他衣袂翻飛,在高臺上有着說不出的恣意風流,他緩緩道:“今日百花争妍,詩宴酣樂,我看這翠竹生于江畔,無絲竹悅耳,也無群芳相伴,終日所見,不過滔滔江水,實在是太過孤寂。”
他聲音漸漸低下來,用無限趨近于溫柔的聲調,輕聲說:“于是——便把今日所得全數贈與它們,也叫青竹,能在春光裏有所相伴,不至于寂寞。”
衆人便輕松地笑起來,笑鴻胪寺主簿的風雅知趣。諸青坐在案邊,寬袖下的手指在微微顫抖,她知道這番話他只說給自己一個人聽。
他們一路走來,不求長久,只願對方在某些本該快樂的時刻,不至于太過寂寞。
這便足夠了,在高朋滿座中,他将滿腔的溫柔說得隐晦又盡興,只要她能懂得,便足夠了。
那是他們最後一次見面,六天後,諸青在家中阖上了眼,她死的時候,蘇松雨不在她身側。
這是她有意為之,她到最後都不敢對他報以同樣的熱烈,也不願真切地面對他因自己而心碎,她沒有讓任何人知曉,包括他。
她其實十分懦弱,所以七年前那個秋天,當少年推開了她的門,跌跌撞撞地說要她跟他走,不顧前程也不計後果。她為這份幼稚而坦蕩的勇氣心動,那是她從始至終,都未曾擁有過的。
他們的故事就到這裏。
從春到秋,長安的花開了又謝,那些未能說出口的無用的深情,也該随着時間,慢慢湮滅在風中,直至消散不見。
但是蘇松雨沒有。
諸青死的那一年夏,他找到了芙瑤,他知道她和芙瑤的關系,也知道把這位歌姬救出栖雲樓,是她一直以來的願望,她已經不能再完成這個願望,但他還可以。
他帶了足夠的錢財,貌美的歌姬卻只是輕蔑,她說她的名字被記載在戶部的冊頁中,根本無法輕巧脫身,再多錢財也無用。
于是他們相對着無言,片刻安靜後,芙瑤突然笑着說:“有沒有人說過——你們很是相像?并不是長得相像,是你們都有一種特別的氣度。”
她看着眼前依然英俊,但眼神中只餘疲憊的青年,她一邊笑,一邊流淚:“明知不可為,卻還作努力,你們在說這些話的時候,真的十分相像。”
蘇松雨在這句話中長久地沉默。
那天晚上,他在栖雲樓中放了一把火,芙瑤事先就帶着樓中的姐妹們逃了出去。她們積累的錢財過去都偷偷放在諸青處保管,如今他代替她,将它們全數還給了伶人們,還加上了自己的贈與。有了這些錢,她們會過得很好,離開長安,在哪裏都會過得很好。
火從子時燒到東方既白,把長安曾經醉生夢死好去處的栖雲樓,燒成了一片焦黑的殘垣。
再沒有栖雲樓,再沒有臨風臺,沒有初秋時候醉中的相遇,也沒有暮春時節風中隐晦的話語。
人間惆悵事,長安從來不缺。
蘇松雨已經準備好面對事發的後果,即使那晚燒死的全是老鸨嫖客,但縱火罪不會被輕描淡寫帶過。
一個人救下了他,太傅之女傅雨棠,也是滌塵齋的主人,諸青的生前好友。
太傅之女手段通天,她保住了他,還找了個樓中已經被燒死的嫖客當了替罪羊。滌塵齋二樓的茶室內,她身邊還有一個年輕的女道,她們看着怔忡的青年,唯有長長地嘆息。
他們說了一下午的話,話題關于那個在暮春辭世的女子,說她生前的諸多坎坷,說她在颠沛流離之中愈發沉默隐忍的性格,說她從始至終的堅韌,也說元化十年早春,他在街對面,她在二樓,柳絮漫天的春風中,那場不為人知的相遇。
他們談了許久,談到他的心越來越空,除了鈍痛,別無一物。
臨走時,蘇松雨向那位女道請詢了一個問題。
“道長是昆侖宗人,可算命蔔卦的本事,卻是須節宗的……”
女道挑了挑眉,她說須節宗宗主同她有交情,是以她精通須節道術。
青年又道:“須節宗亦以編織幻境,借物入夢聞名,鄙人有一個不情之請……”
“可行是可行,但是此類幻境最耗人心神,一開始不顯,但随着時間推移,入夢者會精力衰竭,甚至深陷在幻夢中,再難醒來,你可清楚?”
“我已清楚。”
“你想好了?不會後悔?”
“多謝道長,我絕不後悔。”
一幕幕畫面在眼前如流水般劃過,清清靜默着看完了這個故事,依附在青年身上,她見到了曾經熟悉的街道,也看到了一些永遠不會再見的故人。
蘇松雨的幻境是記憶,從元化十年到元化十七年,幻境中,他一直重複上演着這七年的時光。
在這裏,他們一次次地相遇,一次次地交集,他有時候會做當年沒有做出的事,比如為她寫熾烈的情詩,為她彈那支他從來未曾送出的《青竹曲》,看着她的眼睛告訴她那些從未出口的心意,可是未等她做出反應,幻境就會崩塌。
是了,如果同記憶偏差太大,幻境會無法繼續,變得支離破碎,他只能被迫着醒來,陪伴着的他的只有空空的帳頂。
所以即便在夢裏,他大多數時候,也在費心扮演一個友人的角色,他們清清淡淡地說話,在靜谧的午後下棋,絕口不提風花與雪月。他沉湎于這般無聊又漫長的夢境,周而複始,沒有盡頭,甘之如饴。
在這個紛亂浮雜的世間,還有一處地方能夠供他徹底的放松,這是多麽不易。
在這個孤苦寂寞的世間,竟然還有一個地方能見到她,這已經是天大的幸運。
即便這份幸運背後是衰竭與死亡,他也無所謂了,如果那一天真的到來,他也會笑着擁抱它,因為他即将踏上真正的尋找她的路途,那是他的歸途。
他投身官場,一改此前清高孤僻的作風,在爾虞我詐中厮殺出一條通坦路途,三十五歲就當上了少卿。手握權力的蘇松雨,把當年她父母的案件從頭到尾再推翻,徹底地洗清了曾經的污名。
他又接手了滌塵齋,花了相當多的人力與錢財印刷她生前的作品,無論是詩歌還是小品文,他希望這些凝結着她心血的字句,承載着她思想的墨痕能夠傳播到更廣的地方,他希望世間能有更多人懂她。
這些事并不算輕松,但蘇松雨深深知道,這些對于已經故去的人而言,已經是微不足道了。
他其實是在借此舒慰自己,舒慰那些遲遲不肯消散,時至今日仍頑強紮根在他心底的、無望的情意。
元化二十九年,蘇松雨身體日漸虛弱,他知道原因是什麽,但他仍未停止。
第二年春,他告了假,從長安出發,帶着那把名叫“流雲”的琵琶,順着江河一路到了隴南。他看見滔滔河水從巨谷之中奔騰而過,水流沖撞在崖筆上的聲響震蕩不絕。
這是她生前心心念念,卻一直無法得見的景象,如今他替她看了,今晚在夢中,他可以向她細細描繪。
接着順流而下,他一路到了青州,他記得那是她的故鄉,可惜她從小便跟随父母來了長安,這些年沒有機會重回故地,而他現在又替她完成了這個心願。
他愈來愈嗜睡,分不清現實與夢境,現在已是元化三十年,但他過的卻是元化十年的時間,他像找不到歸路的游魂,可憐地去尋求那一點點虛無缥缈的慰藉。
蘇松雨已經徹底疲累,對這個世界再無更多眷念。他吩咐老仆将船駛到泰安鎮,那裏有一位他多年前的故交,如果有什麽意外,他是能信得過的人。
清清從幻陣出來的時候,不過過去了兩個時辰,但她卻看盡了一個落寞之人的所有的心事。
她睜開眼,長久地注視着榻上閉目的男子,清清想起了那句詩。
“風起松愈靜,雨來竹更青。”
這句詩用來贊美十七年前那個芝蘭玉樹般俊美的探花郎,在那一年,它傳遍了整個長安,所有人都在談論他青松般的氣度,明月般熠熠生輝的詩文。
但沒有人知道,這裏面除了蘇松雨的名字,還有另一個人的名字,她的名字藏在這句詩中,也在人們口中傳頌,像花瓣随着風飄向遠處,像夜雨靜悄悄地來去。
他們的名字克制又纏綿,在短短十個字中,悄聲道盡了所有不能逾越的距離,并且不為人知曉。
作者有話要說:??這章寫得我狠狠傷了,必須好好休息十小時(明晚見)